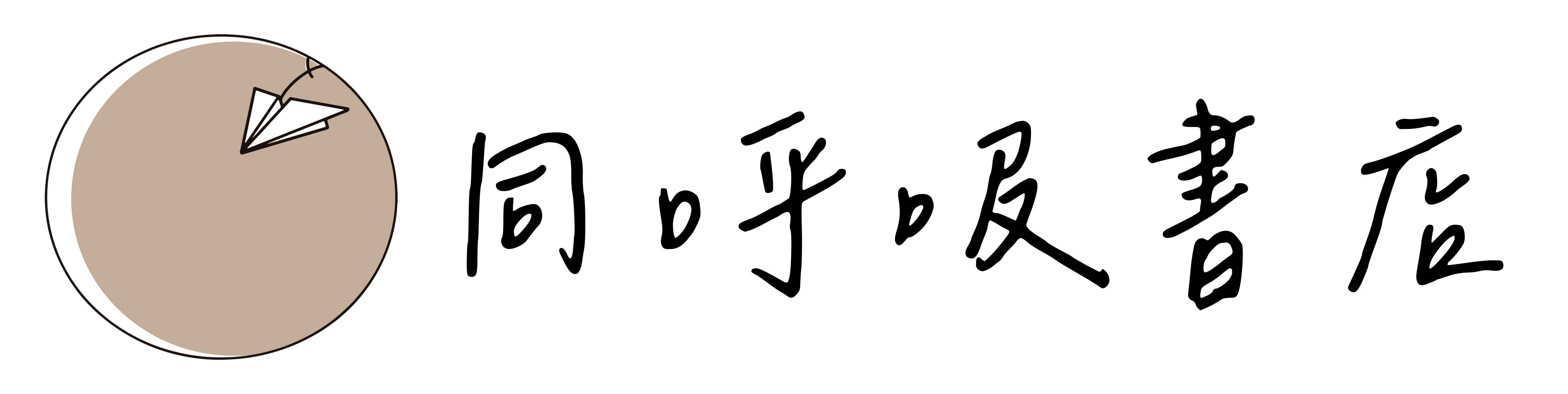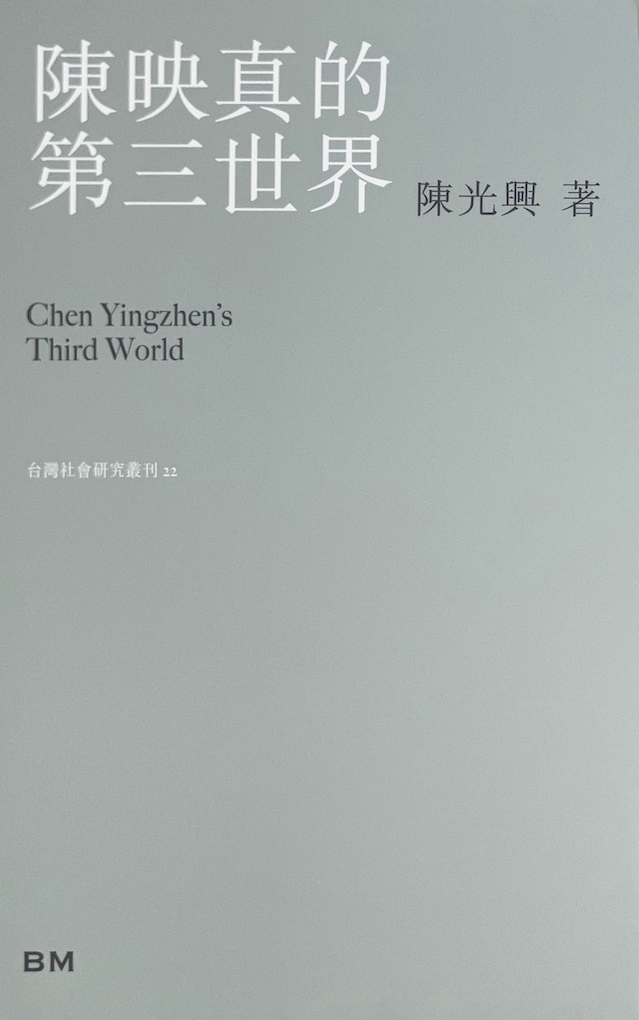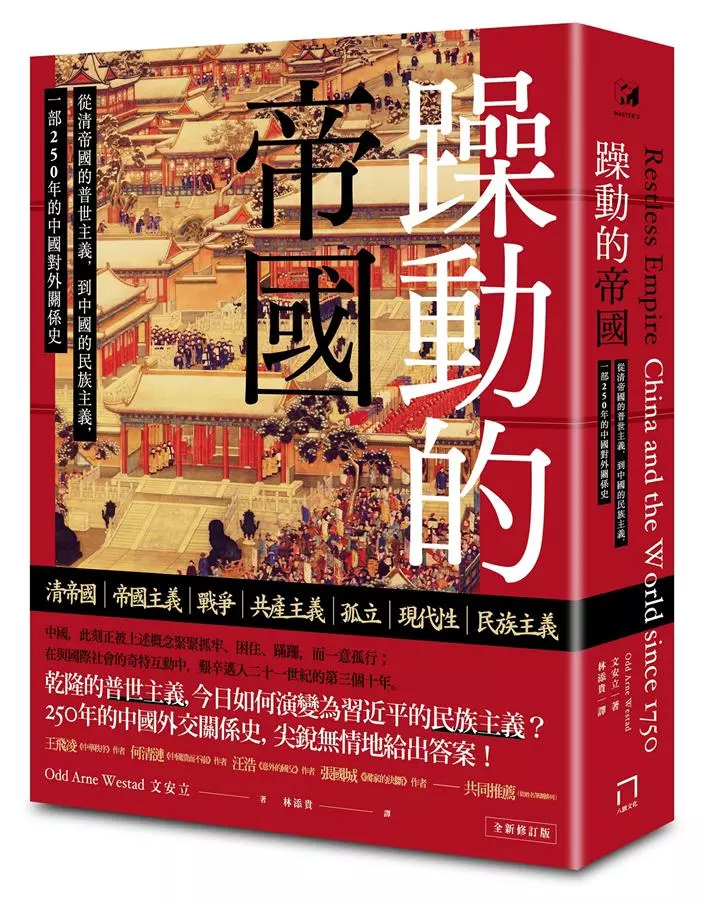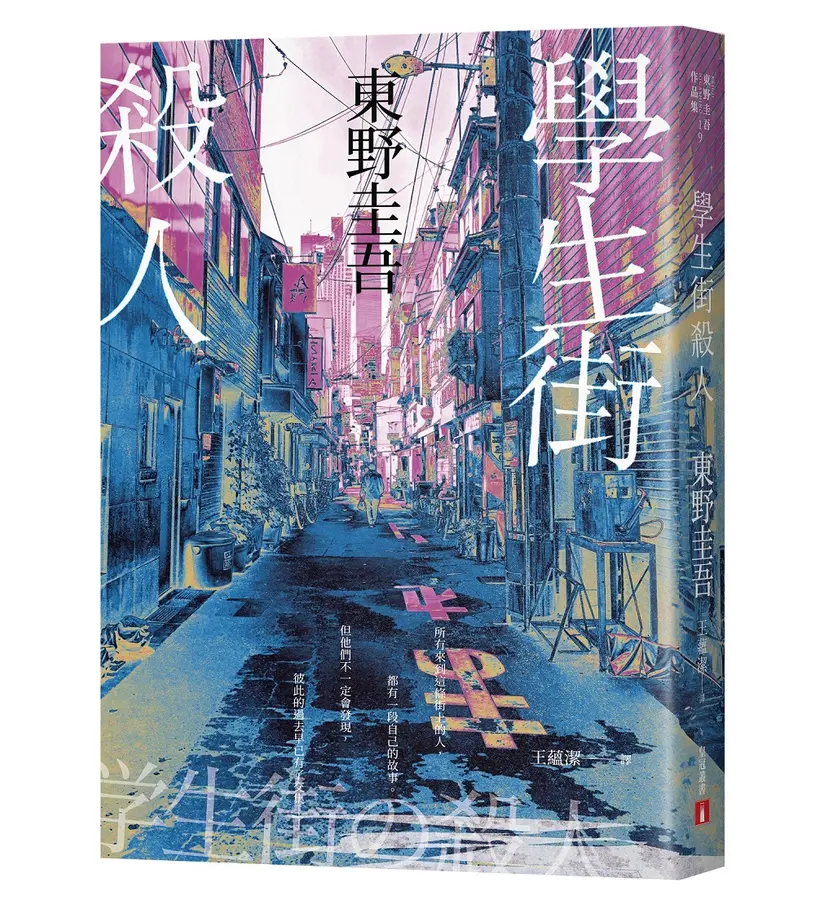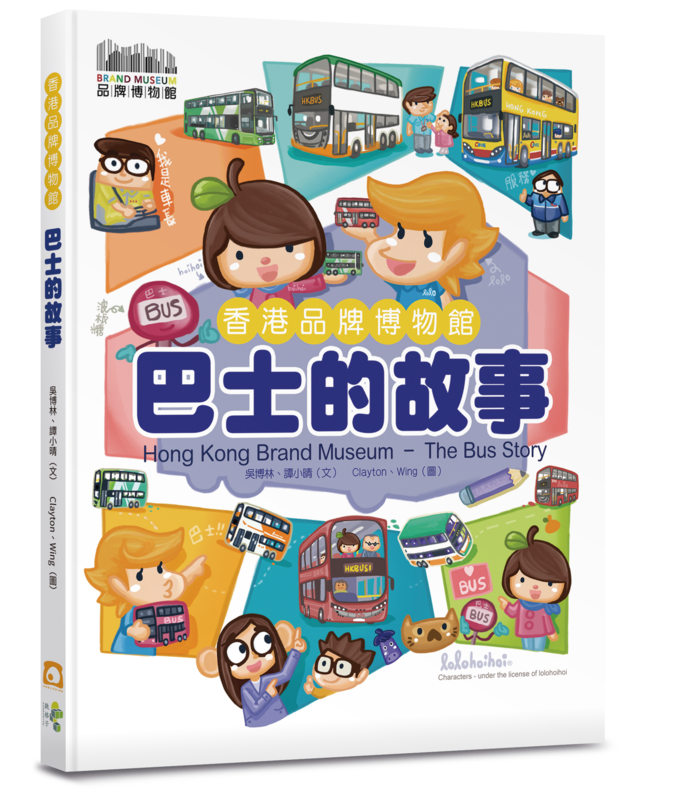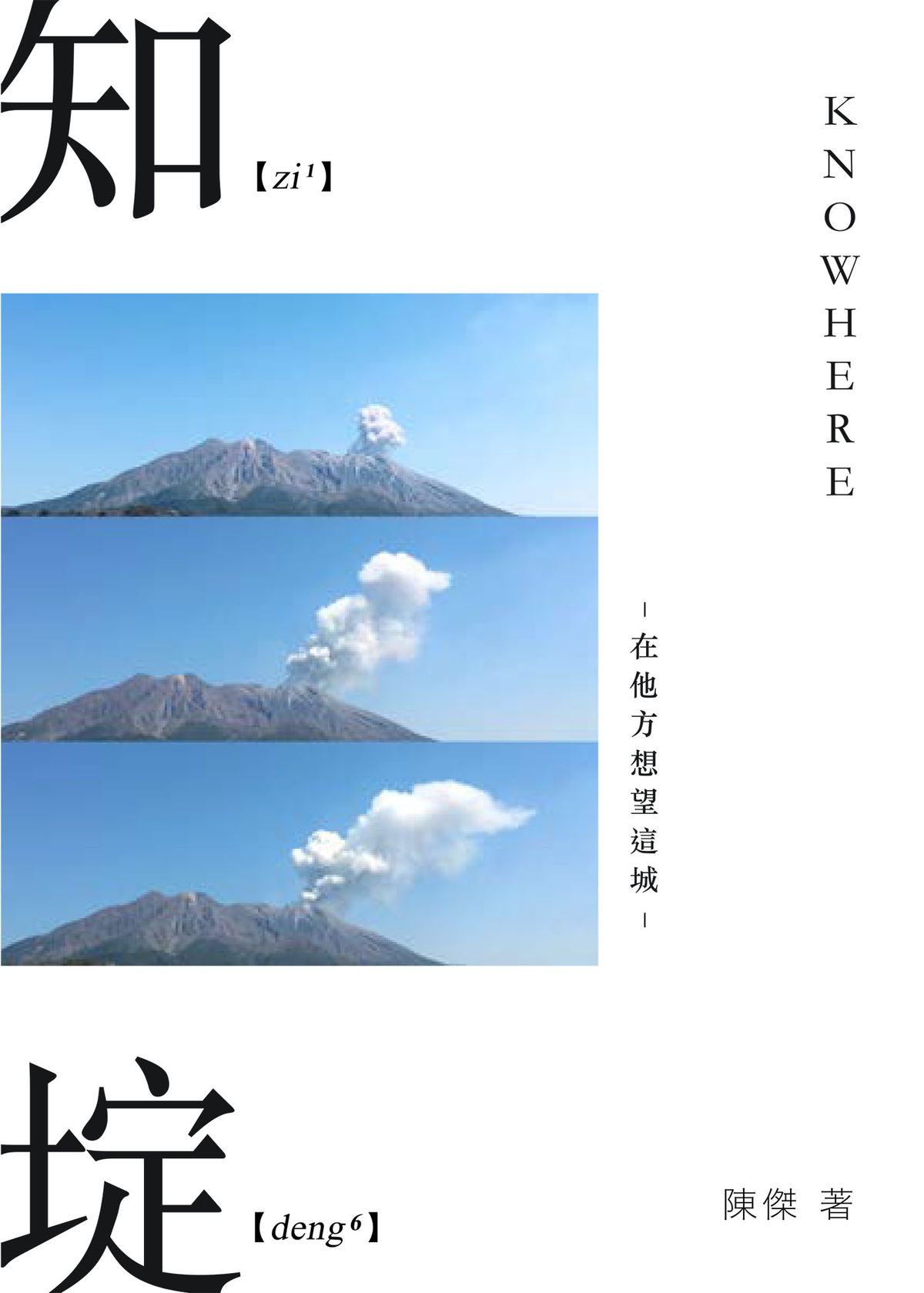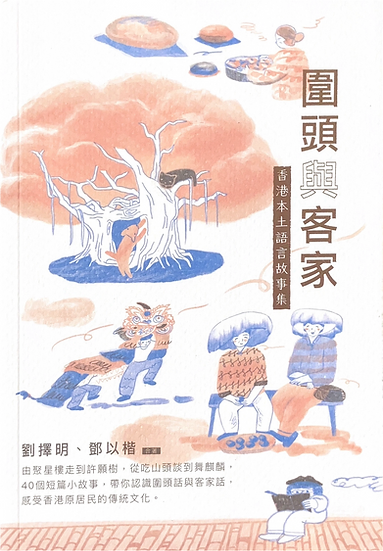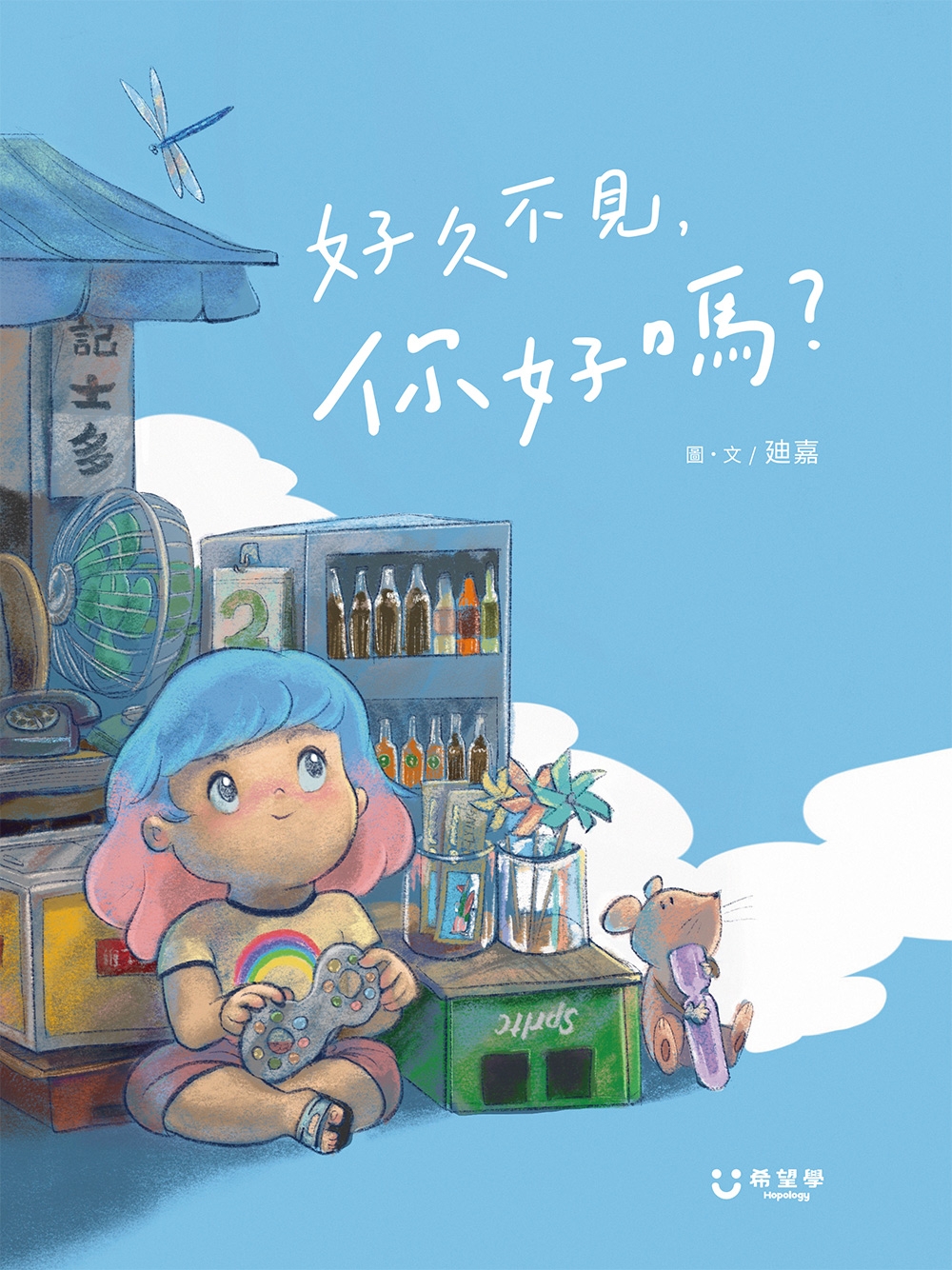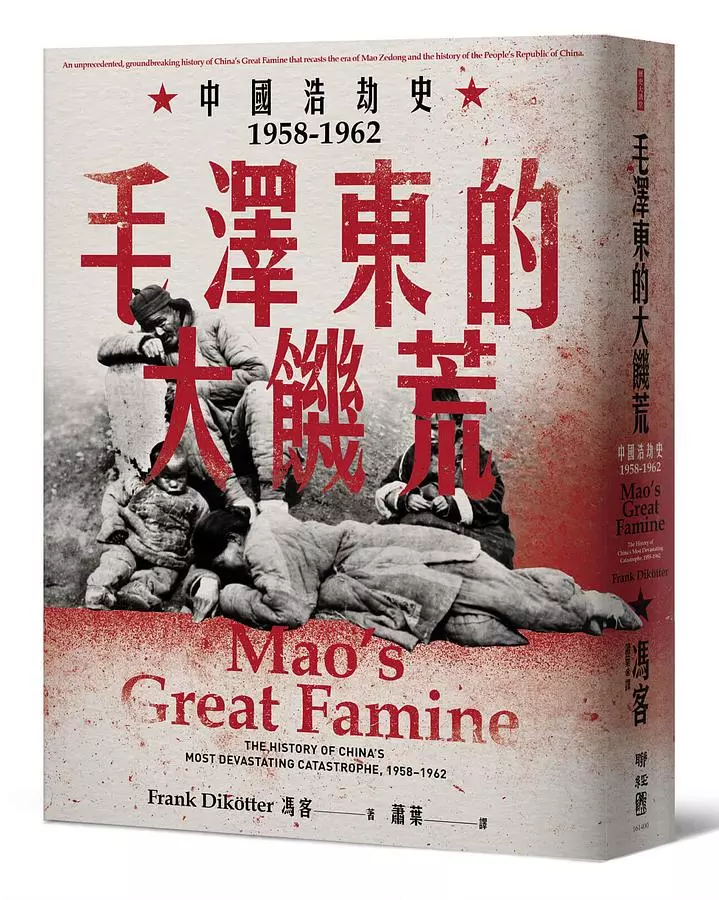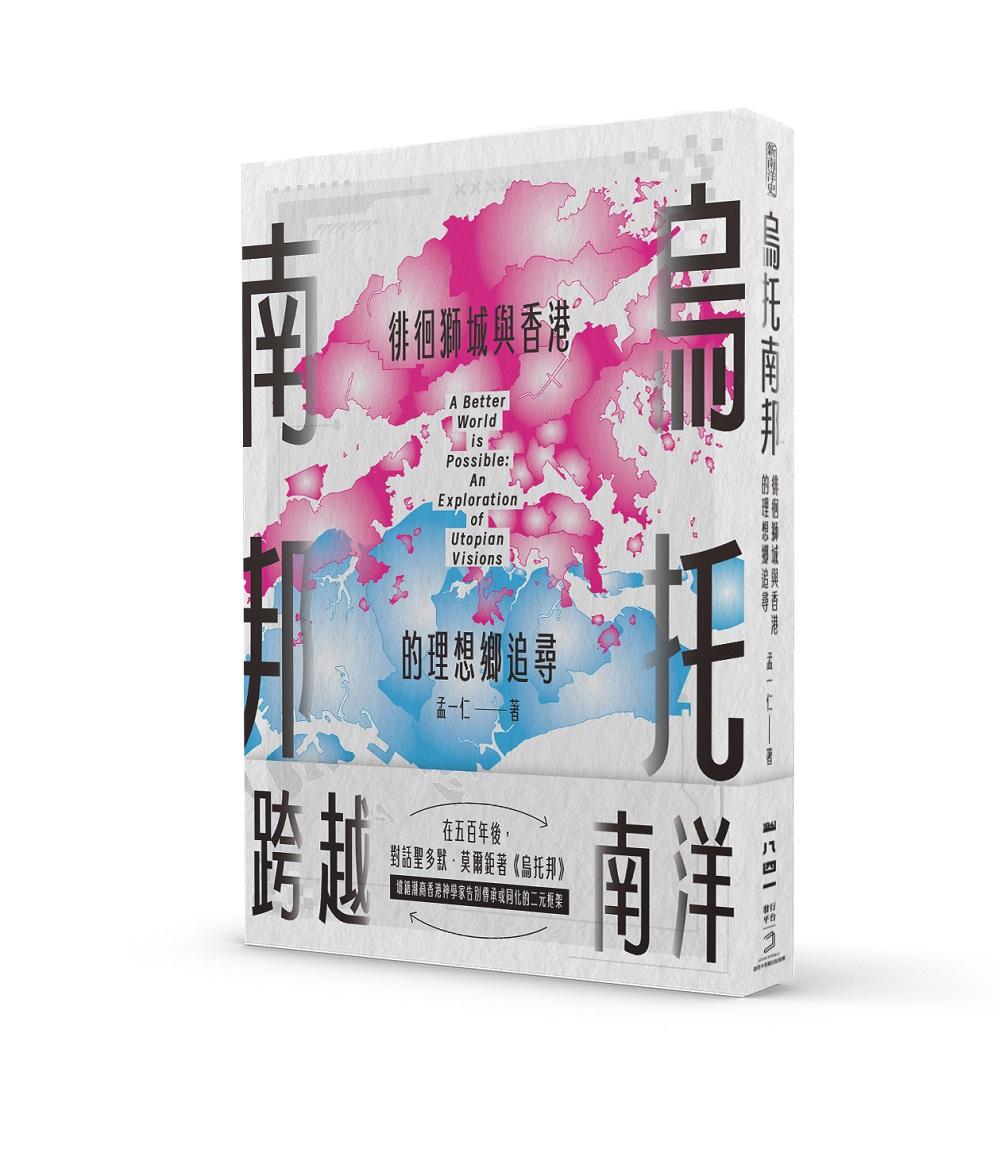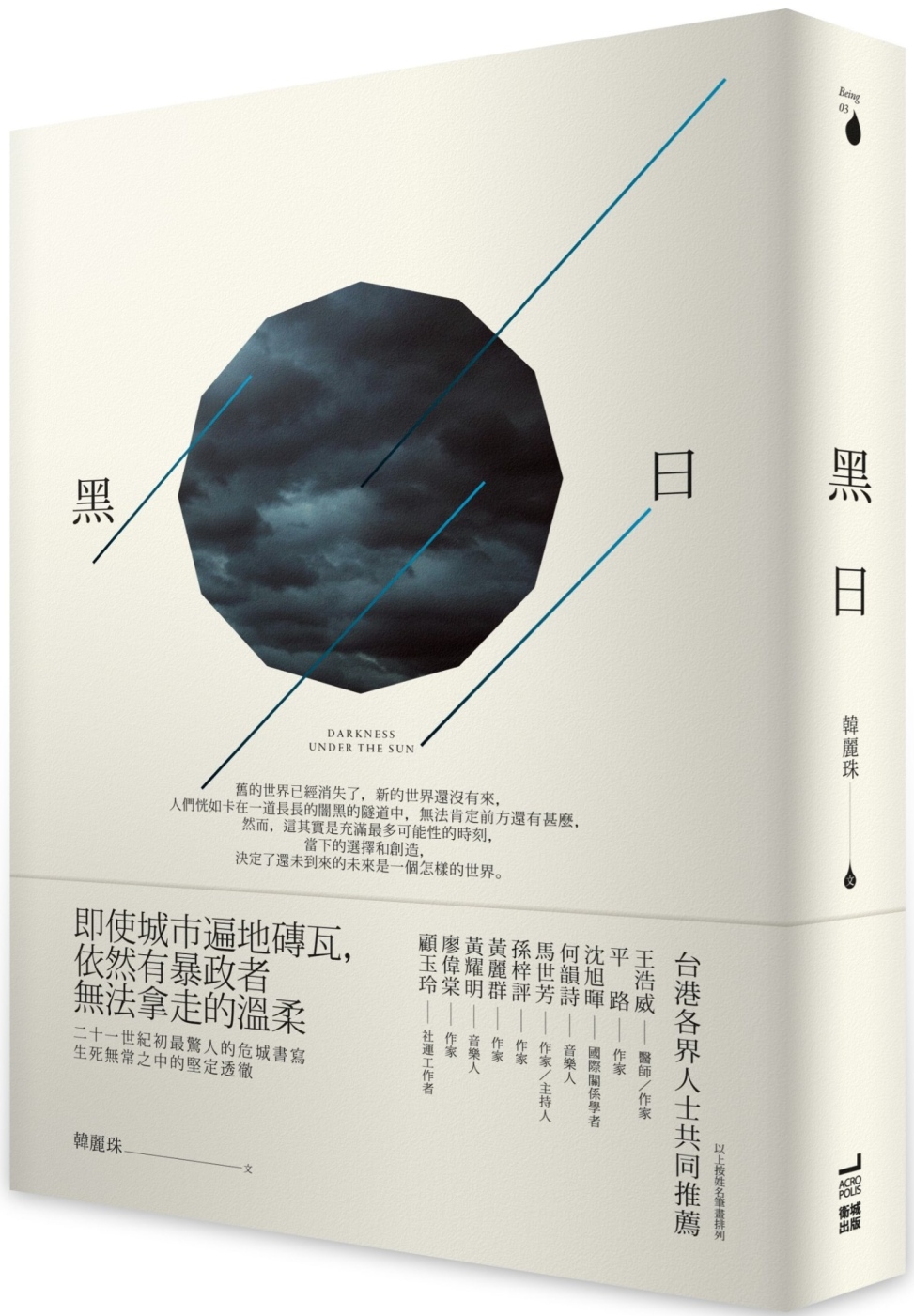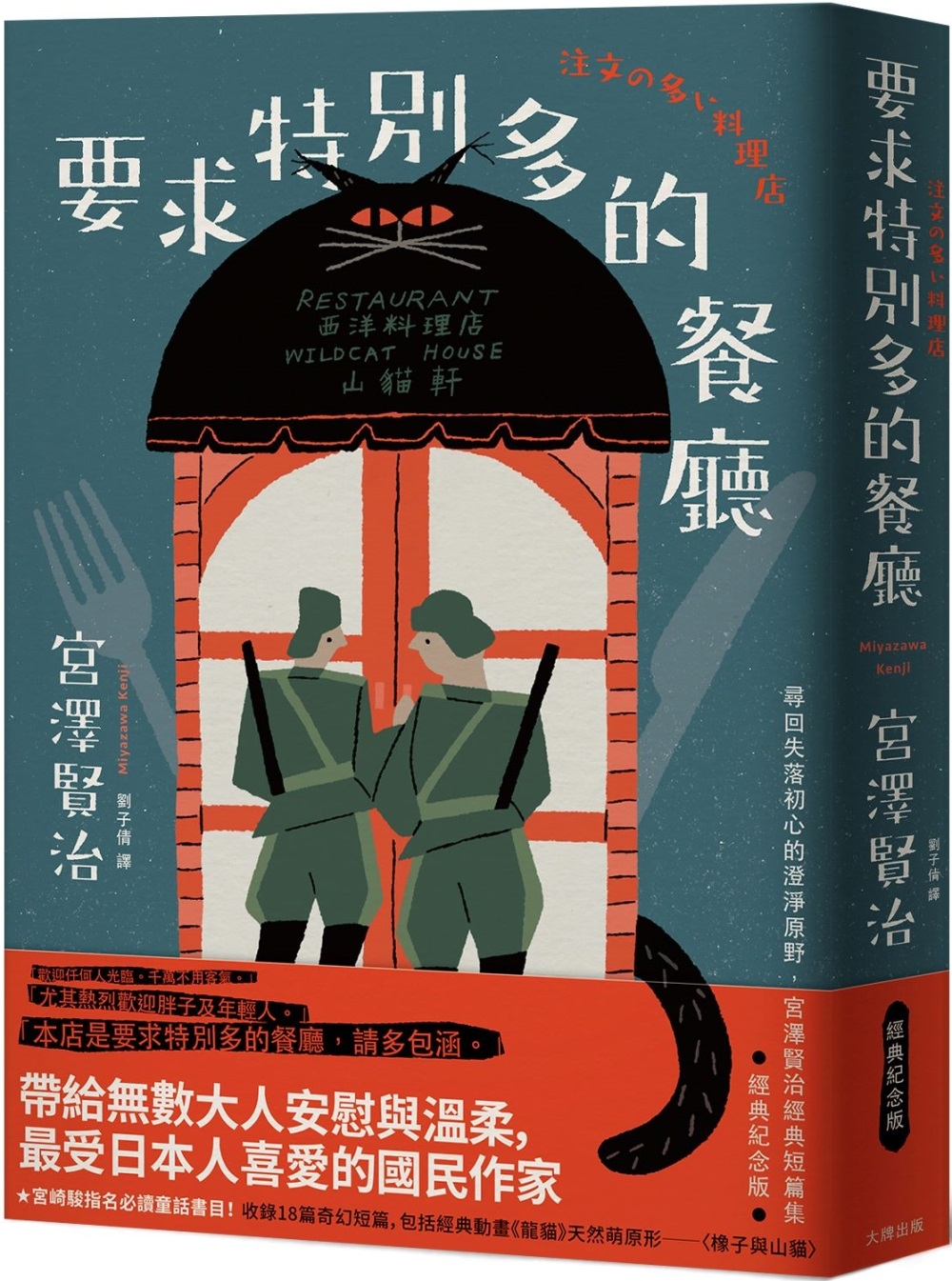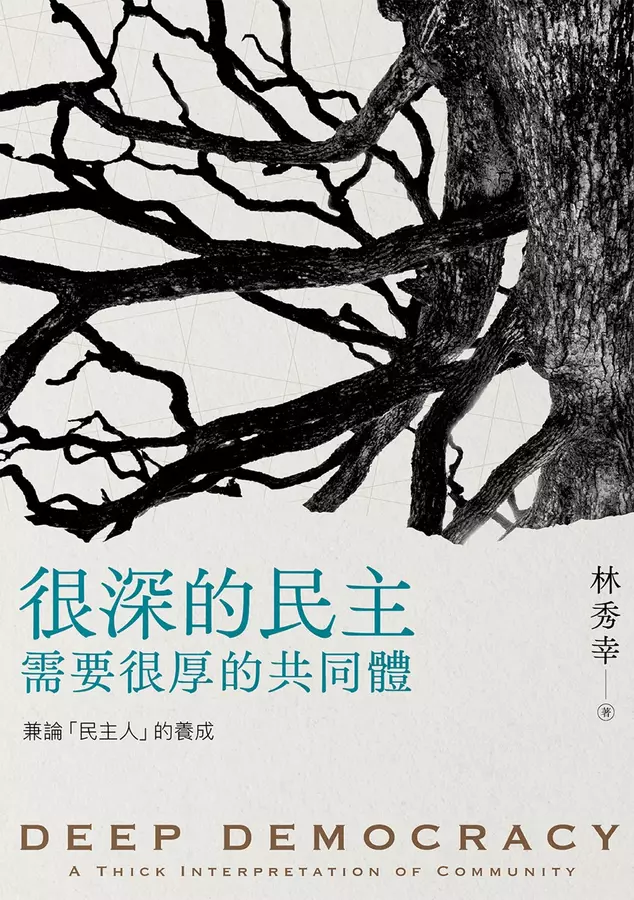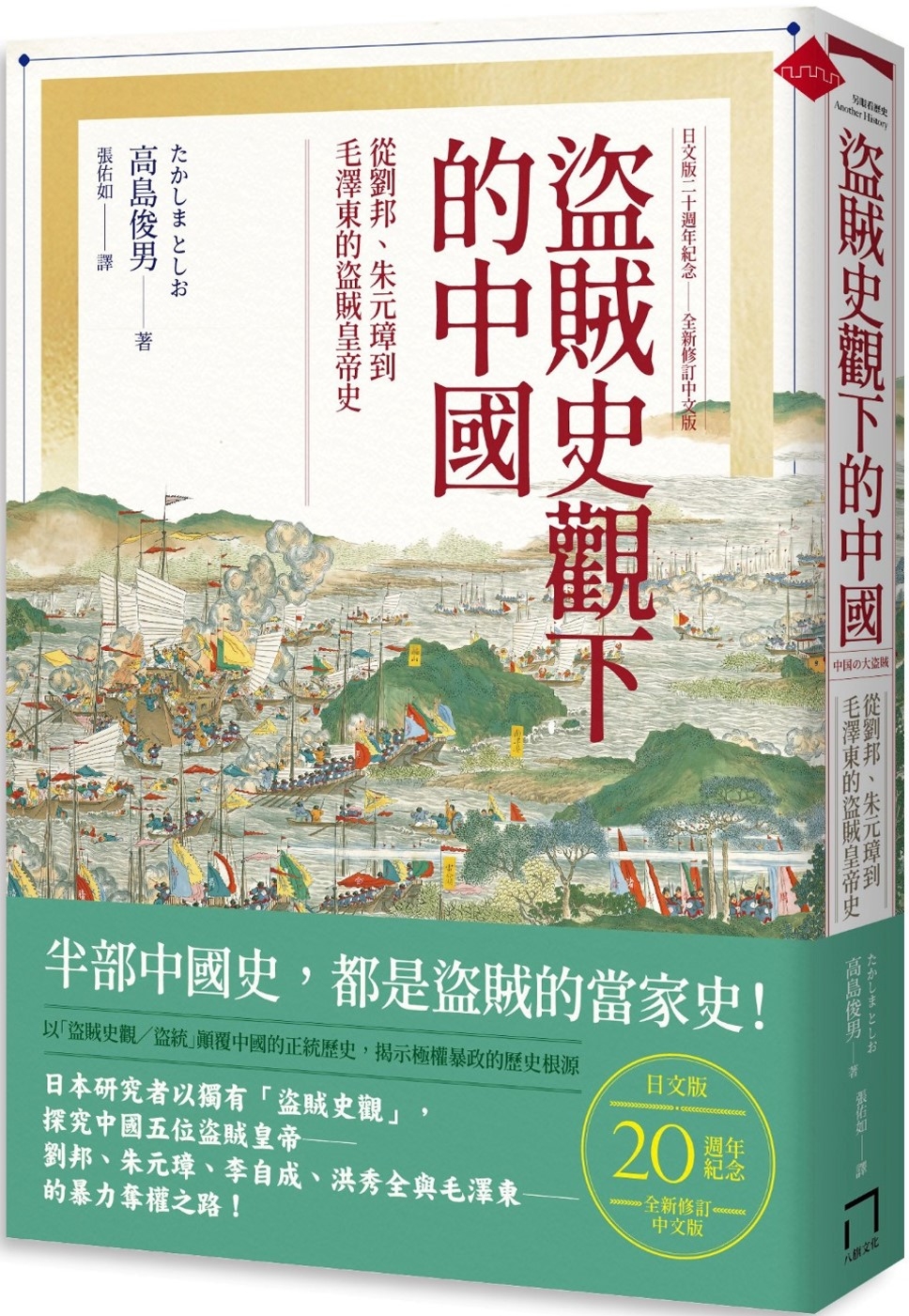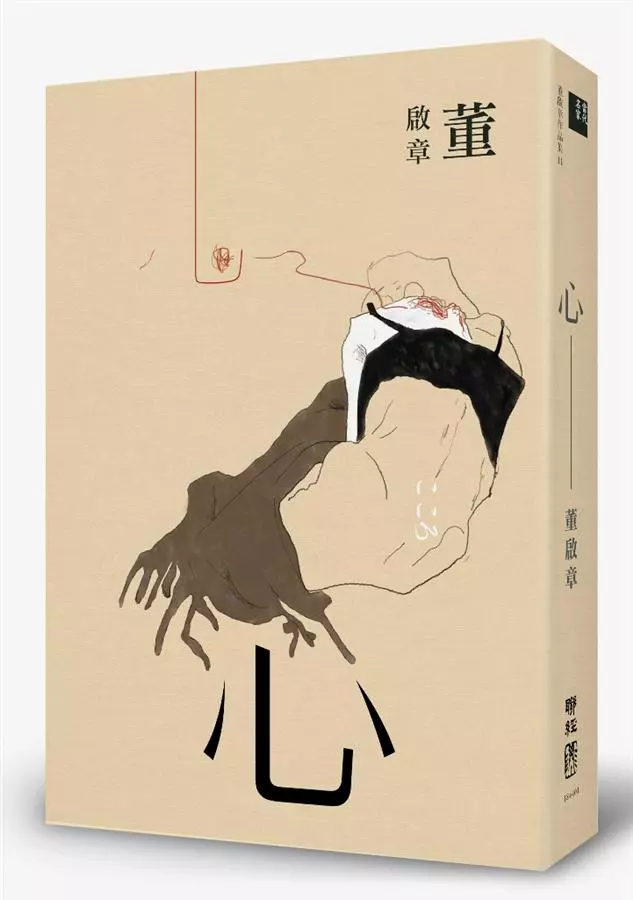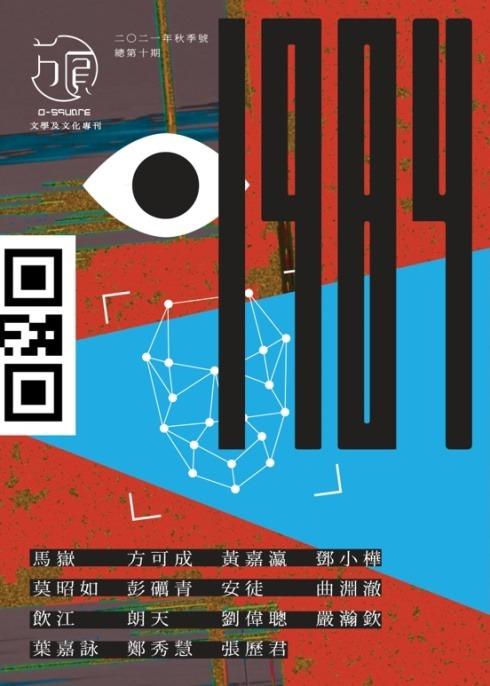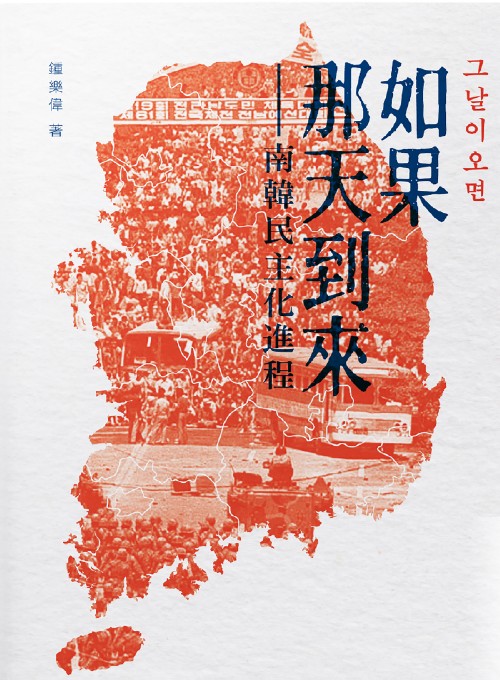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到底意味着什麼?對我而言,他所謂的第三世界是職後新殖民主義時期的後殖民性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在反殖民獨立戰爭、內戰中慢慢走出來,不論以「富國強兵」或是追求國家現代化為動力,被立即且快速地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及其內部與之抗衡的社會主義陈營,所構成的二元對立的全球冷戰體制中。
第三世界問題的歷史縱深達達大於歐洲經驗繁衍出來的左右問題,無論左右是真還是假問題,能否面對其自身環境的複雜性是困難的問題,而西歐、美國之外的地區真能夠全然收攬到不屬於我們歷史經驗所派生出的左右世界觀?難道左右問題不是實本帝國主義「同一個」問題結構,因而遮蔽了歐洲本身及其之外歷史經驗的追問?就像民族國象問題是歐洲歷史的產物,為什麼其他地區可以不經思索地套用在自己身上?無數的問題可以繼續推演,於是就開始陷入普逼主義與特主義的論辯,於是跌入另一個預先套好的陷阱。
第三隻眼的直覺是:陳映真洞察身邊的能力讓他長出了另一隻他自己都沒法充分意識超越左右的眼睛,這隻眼睛不特殊,其實內在於「第三世界」的需要,必須回歸歷史客觀狀態的複雜性,迫使要介入的有心份子能接地氣、著陸、低空俯視自身的大地,「思想」的特定性才是「我們的」。
本文書寫的動力,是希望台灣批判的學術思想界能夠認識自身的第三世界歷史屬性,期許中國大陸知識界不要丟棄第三世界的屬性與思想資源,要保留第三世界想像的香火,擴大我們極為狹窄的知識對象,使得他者與自我能夠更為開放、更為多元。
序一 從去帝國到重新發現陳映真(鄭鴻生)
——陳光興的心路歷程
序二 粗大的箭頭(王曉明)
導讀 第三隻眼
一 狂人/瘋子/精神病
二 五〇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
三 解放分斷體制下的「本/外省失鄉人」
四 社會主義、去殖民及其困境
五 回到萬隆主義的路上
跋 死亡作為方法的政治思想
參考書目
這是作者再一次以其不安的心靈,深刻的自覺,苦心孤詣,尋求真正解放之道的困思之作。作者企圖擺脫形形色色意識形態的桎梏,以及五花八門的西方理論框架,直接面對「帝國 / 國族」的致命吸引力,來為這戰禍罩頂的台灣與危機四伏的兩岸關係,以及百多年來陷入紛亂迷失的整個第三世界,找出一條生路。但作者並不想刻意保持某種批判的距離,也不想從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來「超越」這時代的紛爭與難題,而是藉由台灣豐富的在地資源 ─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創作,直接進入衝突核心,深入到具體、分歧而多樣的生命欲望底層,包括作者自身的多重身份糾葛,及其恍若哪吒 / 孫悟空再世,與世俗的扞格、衝撞與越軌,來面對內在的矛盾與本相。這裏是一場以貼身對話、自我質疑及反覆問難的纏鬥方式來進行的肉搏戰,企圖從我們自身最根深蒂固的執著中殺出一條血路。讀這本書將是一步步心靈解放的體驗。
——鄭鴻生
這是陳光興繼《去帝國》之後的又一本傾心之作。全書分為七篇,晃眼一看,你可能會以為這是一本陳映真論,不過,翻開其中任何一篇,認真讀幾段,你就會發現,這是一本無論寫法還是內容,都相當特別,絕非可視為一部作家論的書。我用「傾心」二字,不只是因為它成書的時間相當長,差不多有十五年,更是因為,這並非一本只是坐在書房裏勤奮思考寫出來的書,它的書頁裏滿佈著作者二十多年在東亞各地乃至中東、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區「遊走」的印跡,是一本用他在這路上持續積累的感受一遍一遍澆壘而成的書。對於陳映真,光興並不持一種信徒式的侍奉左右、寸步不離的態度,他似乎更像一個雲遊的行者,懷揣對祖殿的敬意,不斷走向新的遠方,一面展開對陳映真的細密的引述和分析,一面卻不斷地離開這種引述和分析,他當然會回來,但又會再走開⋯⋯也就在這來來回回之中,一種散漫不羈論述的豐富,一種在虛構與親歷之間自如的串聯,那些刺激你定睛關注的斷言,都一齊湧出了紙面。
——王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