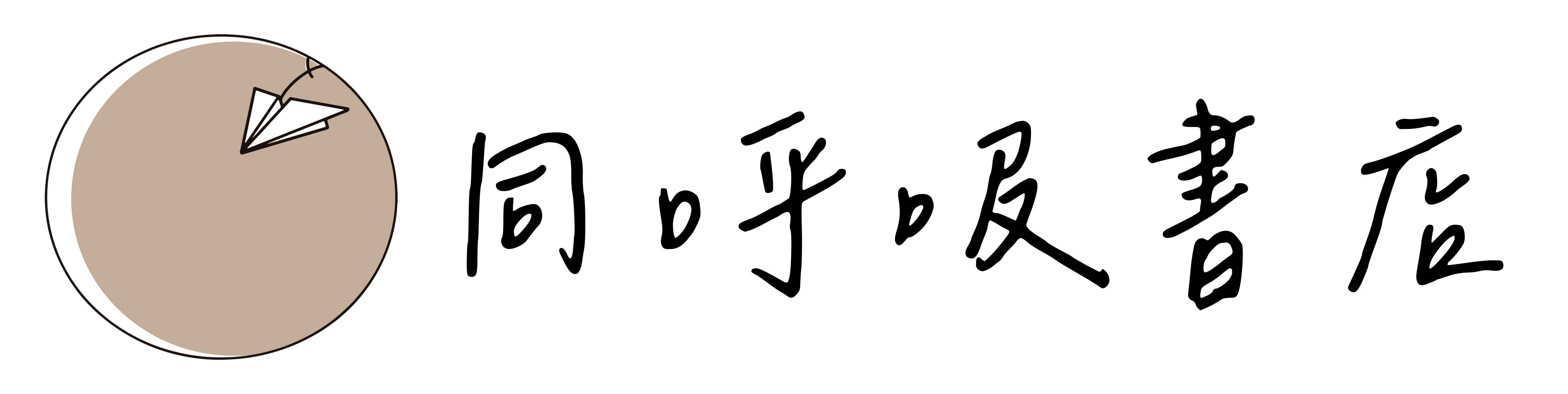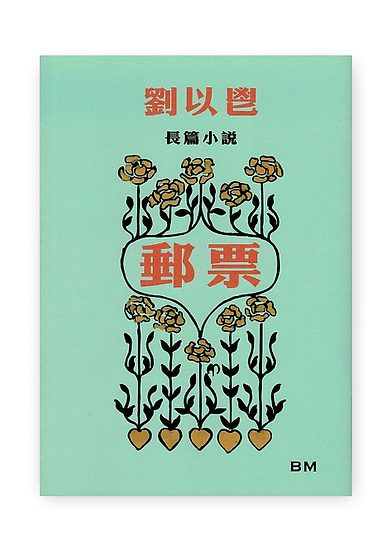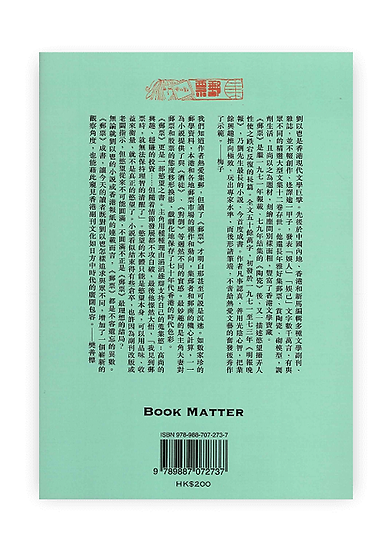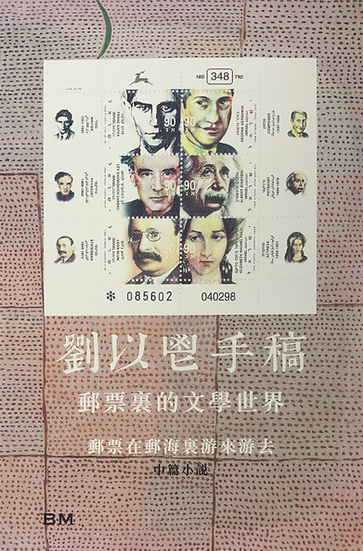劉以鬯是香港現代文學巨攣。先後於中國內地、香港和新馬編輯多種文學剛刊、雜誌,並不輟創作、迻譯逾一甲子,發表「娛人」「娛己」文字數千萬言,有與眾不同的精選大型文集十二卷存世。他還長年雅好集郵票、賞陶瓷、砌模型,調劑生活,且尚以之為題材,刻繪塵間別樣面相,豐富了香港文學寶藏。
《郵票》是繼一九七一年報載、七九年結集的《陶瓷》後,又一描述慾望撥弄人性使之跌宕反復的長篇。全文五十餘萬字,初發於一九七一至七三年《明報晚報》,乃劉先生最長的小說,今首度成書。作者凡事認真,善用光陰心智,把業餘興趣推向極致,玩出專家水準,而後形諸筆端,不啻給熱愛文藝的奮發後秀作了示範。
——梅子
我們知道作者熱愛集郵,但讀了《郵票》才明白那甚至可說是沉迷。如數家珍的郵學資料,本港和各地郵票市場的運作和動向,集郵者和郵商的機心計算,一一為小說提供了與《酒徒》、《對倒》等迴然不同的實感。最妙趣的是主角夫妻對郵票和股票的態度移形換影,戲劇化地保存了七十年代香港的時代色彩。
《郵票》更是一部慾望之書。主角用種種理由滔滔雄辯支持自己的蒐集慾:高尚的興趣、穩賺的投資……但隨着情節發展都不攻自破,最後他憬然大悟,「我見到郵票時,就無法保持理智的清醒了」。慾望的本體只能是慾望本身,可以用品味、收益來衡量,就不是真正的慾望了。小說看似結束得有些倉卒,也許因為剛刊改版或老闆指示,但慾望從來不可能圓滿,不圓滿不正是《郵票》最理想的結局?
無論就劉以鬯的小說或香港報紙的連載而言,《郵票》都是不容遺忘的異數。
《郵票》成書,讓今天的讀者既對劉以鬯怎樣追求與眾不同,增加了一個嶄新的觀察角度,也能藉此窺見香港副刊文化如日方中時代的廣闊包容。
——樊善標